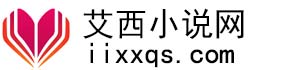50-60(15/29)
你最敬仰的老师,死于我父亲抄斩的后两年,你问我为何如此问?
“如今我做了老师,才知晓师生情深,若我猜测没错,那夏炎指挥使于你而言如师如父,你年少时失去他,独自一人行走这北镇抚司,如今高至镇抚使,其中艰辛,难以想象。”
一提起夏炎,倪允斟神色便认真起来,不再戏谑,甚至浮上淡淡哀伤。
他凄切一笑。
“路途艰辛,不也是走过来了?你倒是调查得深,没错,夏炎对我来说,亦师亦父,不是他,我早和我那幼弟死在了宁中的荒野里,叫野狼给分食了。”见林清听得认真,倪允斟也打开了心怀,鲜少提及的事,也涌上心头,到了嘴边。
或许是情意作祟,又或是互相交换信任,倪允斟怅然道:“他收我为徒,教我武功,带我进镇抚司……可就因为替友人作保,落得个那种下场。昔日里关押刑犯的诏狱,足足折磨他一年多,叫他受尽鼎镬刀锯,筋脉尽断,死无尊严……”
“为了护我,他把我过继到当今指挥使荀虑名下,荀虑将我看的紧,怕我惹出什么事端,又招来祸事。那时,我想尽办法混进诏狱里,就想见一见他…… 或许,若是再不相见,以后就见不着了。”
“你见到了吗?”
倪允斟笑得瑟然,“见到了,那时我十岁,个子小,又对北镇抚司熟门熟路的,在师父几名下属的帮助下,终是在一雨夜见到了……”
“见善,你可知晓,我看到了什么么?”
林清凝眉摇头,此际,倪允斟已是红了双眸,视线氤氲在茶汤漂浮而起的热雾中,飘向极远之地。
“我看到了,无数蛆虫在血肉上钻拱、蠕动,腐肉散发恶臭。他衣不蔽体、湿漉漉地靠在一堵发了霉的墙上,身子骨瘫软,好似摁一摁就可渗出腥黄的脓水来。一道惨淡白光下,他的眼皮耷拉着,可眼睛依旧明亮,还是那个昔日威风凛凛的指挥使大人。我看得见,真的,见善,他还在笑,笑着,却很哀伤。落得那个境地,他似乎一点都不后悔,分明圣上说只要他认个错,承认那林可言的确谋了反,就让他出来官复原职。可他不认,他就是不认。”
眼泪淌落,倪允斟攥紧了拳头。
“他太重感情了,重到轻看自己。”
倪允斟望向林清,颤声道:“所以辛苦算什么?有些痛楚,才要人命。”
“我懂你。”无意识地,林清握住他的手。
“你又怎么能懂我?不过想利用这两分情罢了。”倪允斟悲哀摇头,“不过是利用我对他,对你的这份情罢了。”
林清垂首,微不可察地哽咽了一下,再度抬头,他笑得明朗,“怎么这么说,哪里会是利用,你我志在一处,都是扳倒张党,共谋大事。倘若是利用,也是彼此利用。可我不喜欢这个词。”
他很难掩饰自己发红的眼眶,情真道:“择之,与你相交,我很幸运。”
倪允斟动情地伸出手,撇去林清眼角的泪珠,“既然是幸运,你又为何如此伤感?”
“是啊,为何?我不知道。”
这一次,林清没有躲,他让倪允斟的掌心贴在他的脸颊上,他轻轻闭上了眼睛。
“我自以为有几分懂你,却是半分未曾将你看透。你心里无我,也是应当。”凝视林清,倪允斟平静地说。
“人是不能看得太清楚的,再亲近的人,看透了,也不过是失望二字。”
“那么,隋在山也未曾将你看透吗?”
林清不回答了,他依旧闭著眼,感受倪允斟掌心温度,借此想象阴暗诏狱当中那靠着墙、等待死亡降临的男人。就如同他